风筝鲁迅的写作背景是什么?
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: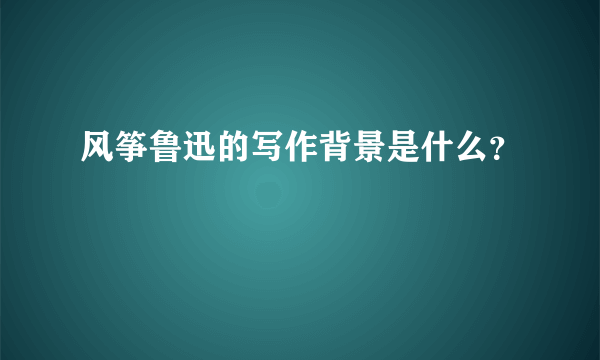
鲁迅在《风筝》一文中讲述了“我”破坏弟弟风筝,多年后又悔过的故事。遗憾的是虽然“我”后来意识到“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,玩具是儿童的天使”,弟弟却对此事毫无印象,因为弟弟“全然忘却,毫无怨恨”,故而“我”无从得到原谅和宽恕。故事以“我”悲哀的思绪引入,又以沉痛的自省结尾,是“儿童的发现”的代表作品。《风筝》创作于1925年,其实早在六年之前,也就是1919年,鲁迅就曾在《我的兄弟》一文中讲述过类似的故事。《我的兄弟》全文如下: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,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。我的父亲死去之后。家里没有钱了。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,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。一天午后。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,看见我的兄弟,正躲在里面糊风筝,有几支竹丝,是自己削的,几张皮纸,是自己买的,有四个风轮,已经糊好了。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,也最讨厌他放风筝,我便生气,踏碎了风轮,拆了竹丝,将纸也撕了。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,悄然的在廊下坐着,以后怎样,我那时没有理会,都不知道了。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。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,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“哥哥”。我很抱歉,将这事说给他听,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。他仍是很要好的叫“哥哥”。阿!我的兄弟。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,我能请你原谅么?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!鲁迅时隔六年重新书写同一件小事,两者有何差别呢?钱理群在《对比解读鲁迅先生和》一文中,对这两篇文章进行对读指出,《风筝》相比于《我的兄弟》,多了“回忆的套子”,以北京冬季天空中的风筝引入,带着“惊异与悲哀”的情绪回顾往事,在故事的结尾,又回到这种“无可把握的悲哀”之中,改单纯的客观叙述变成笼罩在主观情绪下的动情回忆,这是本文最大的特点。此外,《风筝》的描写更加生动、细致、完整,自省也更加深刻、沉痛、复杂。反复强调自己“精神的虐杀”无法弥补,更可见自我剖析之深。最后,《风筝》的结尾处,作者感叹“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,——但是,四面又明明是严冬,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。”钱理群先生认为,雪和冬季代表了鲁迅直面过错的自觉和勇气,使得文章提升了高度。的确,《风筝》似乎是《我的兄弟》的修改版本,但改写后的高度与原作不可同日而语。后世对《风筝》的解读主要突出两点,一是“儿童的发现”,《风筝》中的那句“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,玩具是儿童的天使”被当做主旨来理解;另一点就是鲁迅的负罪感,以及对罪的认定、承担,对赎罪可能性的质疑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两点在原文中也都存在,但尚不够明确的,《我的兄弟》并没有言明“我”错在何处,也没有那么决绝地强调“我”无法被原谅。这两点都是在反复书写中被强化的。那么,这件被鲁迅反复讲述的故事是不是真实发生过的呢?文中的小兄弟,也就是周建人曾有这样的一段解释:“鲁迅有时候,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,或者故意说着玩,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。实际上,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,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,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。”(乔峰《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》),二弟周作人也说:“他不爱放风筝,这大抵是事实”,但鲁迅写折毁风筝等事“乃属于诗的部分,是创造出来的”。(周作人《鲁迅与〈弟兄〉》由此可见,我们不能把文中的“我”与鲁迅完全等同,反对放风筝的故事也未曾真实发生过。鲁迅把“我”塑造成这样一个残暴的长兄的形象,是要强调“我”对儿童的“精神的虐杀”的严重性。“我”虽然并非真实的鲁迅,但何尝不是真实的中国家长们的原型。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裁决儿童们的行为,是长者本位的。这种对长者本位家庭模式的反思,正是鲁迅一辈所做出的的不懈努力。值得玩味的是,《风筝》原文中提到小兄弟“那时大概十岁内外”,既然文中哥哥与小兄弟的原型是鲁迅和周建人,我们可以根据现实中兄弟俩的年龄差推算(周树人出生于1881年,周建人出生于1888年),《风筝》中撕毁弟弟心爱玩具时的“我”也才十七岁左右,尚未成年。然而“我”和弟弟的关系却更像长辈和晚辈,毫无兄弟温情。可见当时作为哥哥的“我”虽然也还是孩子,但却已经进入到严格的长幼等级中,以父兄自居,对弟弟的年幼天真毫无理解与尊重。这让人联想到《狂人日记》中,也有一对兄弟,相比于《风筝》中兄弟的“害与被害”,《狂人日记》中的兄弟关系则是“吃与被吃”。狂人哭诉的那句“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,他也是人,何以毫不害怕;而合伙吃我呢?还是历来惯了,不以为非呢?还是丧了良心,明知故犯呢?”如此看来,这段控诉何尝不适用于《风筝》中的兄弟呢?“我”也曾经是孩子,为何面对儿童,毫无同情与理解呢?“我”也许也曾身处弟弟的境遇,为何轮到自己做长辈时依然这般无情呢?那“吃人”的可怕循环,在每一对兄弟的身上重现。比较《我的兄弟》与《风筝》两篇,有一关键情节是一致的,那就是弟弟对此事的“忘却”。在《我的兄弟》中,弟弟依然“很要好地叫‘哥哥'”,在《风筝》中,弟弟“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。他什么也不记得了”。正是由于弟弟的忘却,“我”的过错才无法弥补,也更能说明传统家庭对儿童的戕害已经成为自然。或许施害者与受害者自己都未意识到这是一种伤害,儿童漫长的成长中,不知遭遇过多少次这样的不被记得的伤害,它们可能永远得不到道歉和弥补,甚至不被记得,但伤害确实发生过,就一定有人受伤。姚丹在《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和文化原罪感》的结尾处这样写道:被吃者和吃人者都处于不自觉状态中。当“我”已经意识到了“我”当初行为的虐杀性时,被虐杀者却毫无痛苦,历史之错从何处去改正?因此,《风筝》文末“我”的悲哀,并不仅仅是个人没有求得宽恕的“难过”,而更是对历史中“精神虐杀”事件的无影无踪,不得求证,也就无所谓改过的悲哀。在这里我们大胆再进一步追问,周建人回忆称,鲁迅破坏风筝并未发生过,不是恰巧和故事中弟弟的反应一样吗?有没有可能是周建人真的忘记了这次伤害呢?真相我们不得而知,风筝的故事也在真实与虚构之中不断摇摆躲闪,也许只有“忘却”才能将二者平衡,也只有“忘却”才能突显“伤害”。在《狂人日记》中,当狂人意识到自己的哥哥也参与了吃人时,这样感叹道:“吃人的是我哥哥!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!我自己被人吃了,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!”在文章结尾,狂人自省,或许“我未必无意之中,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,现在也轮到我自己……”由此人们看到鲁迅思想中的原罪意识与忏悔精神,《风筝》中的弟弟是否也如狂人一样,携带着“吃人”的基因,在无意中也曾吃过人?此外,我们不难理解,弟弟“忘却”这一情节的设置,也是作者对自己的无情与鞭笞。这是颇具鲁迅风格的“永不原谅”,丝毫不给自己被原谅、被宽恕的机会。“现在,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,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,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。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,——但是,四面又明明是严冬,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。”据钱理群先生的解读,这严冬是一种“敢于正视现实生活的严峻,并在痛苦的反抗、挣扎中获得生命价值的冷峻的情感和人生态度”,是如同散文《雪》中描写的北方严冬一样的境地,是一种决绝的情感取向。作为《野草》中的一篇,《风筝》情节简单、平白易懂,似乎与其他文章风格不符,但如此细细读来,理解文章背后的沉重和深刻,确有“野草”的某种印记。这肃杀的结尾和决绝的态度,是与“野草”一脉相承的。把《风筝》放回《野草》这本集子里去理解,也许会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篇文章的独特性和连续性。



